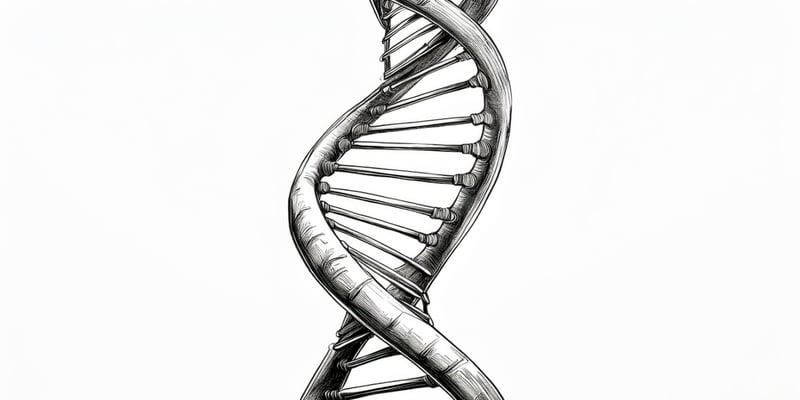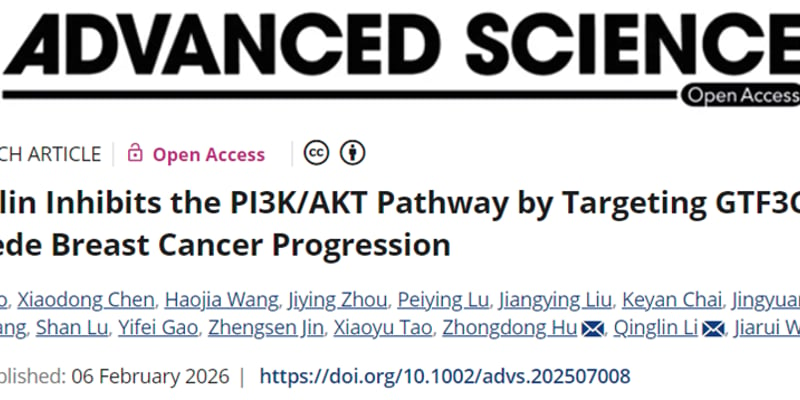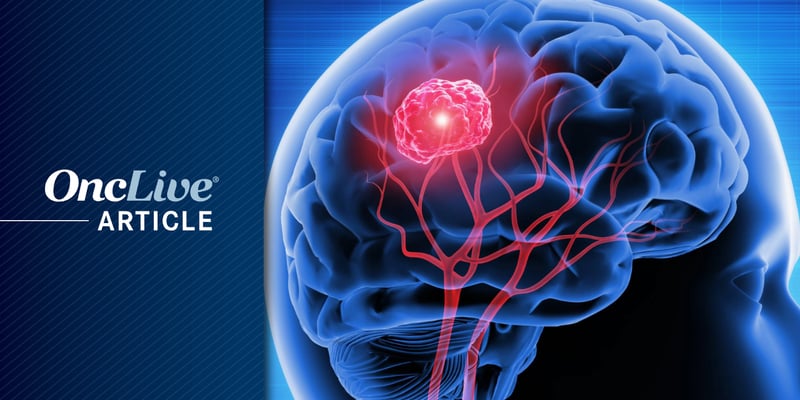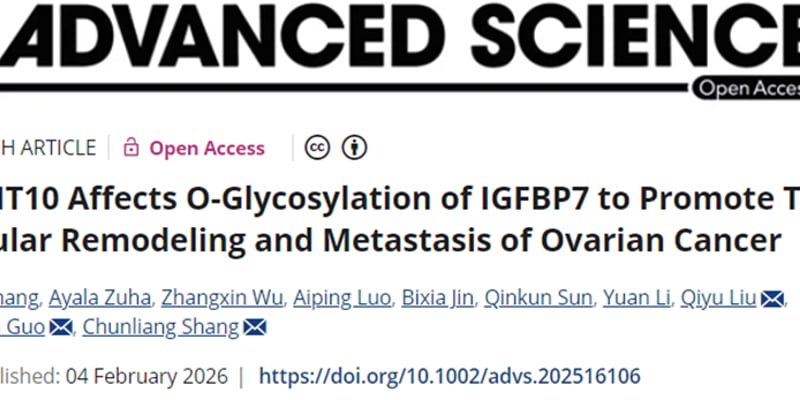尽管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显著改善了许多肺癌患者的生存预后,但这些先进疗法也带来了不小的代价,不仅是经济负担,还有累积性和长期的治疗毒性。那么,对于癌症治疗来说,“更多”真的总是“更好”吗?患者是否有可能通过接受“更少”的治疗而同样获益?
在2025年欧洲肺癌大会(ELCC)上,Benjamin Besse医学博士发表了关于肺癌治疗“减量”(treatment de-escalation)策略的理由和方法的专题演讲,挑战了癌症治疗中“越多越好”的传统观念。其他专家也在接受采访和会议讨论中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为何考虑治疗“减量”?
Besse博士强调:“减量试验是必要的,但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和所有药物。它必须基于强大的生物学和药代动力学原理。”
他解释说,减量的概念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印度,只有2.8%的人能够负担得起免疫治疗,”他在演讲中指出。这一数据凸显了尽管尖端疗法在高收入国家唾手可得,但对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来说仍然遥不可及。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温希普癌症研究所执行主任Suresh Ramalingam医学博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他在采访中表示:“不幸的现实是,许多国家的患者无法负担最先进的肺癌疗法。‘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的需求正在推动研究探索更低剂量的可能性。”
Besse博士认为,减量策略可以在不损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帮助患者避免不必要的毒性,减少住院时间,并显著降低医疗成本。
他在演讲中概述了减量的几种方法:剂量降低(使用较低剂量但仍保持药物疗效)、延长治疗间隔(延长两次治疗之间的时间)和缩短总疗程(缩短整体治疗周期)。
剂量降低的生物学依据
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和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剂量降低的生物学依据在于,这些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断T细胞上的PD-1受体发挥作用,而达到受体饱和所需的剂量相对较低。
Besse博士引用了研究数据,表明即使以1 mg/kg的剂量每3周给药一次,帕博利珠单抗也能使外周T细胞上的PD-1受体达到饱和。
他还引用了另一项数据,显示单次输注10 mg/kg的纳武利尤单抗足以在长达80天内占据T细胞上超过70%的PD-1分子。
Besse博士指出:“单次注射10 mg/kg的帕博利珠单抗就能使淋巴细胞上的PD-1饱和400天,然而我们却每21天给药一次;这似乎不太合理。”
在黑色素瘤患者中的研究显示,0.1 mg/kg的纳武利尤单抗(标准剂量的30倍)达到了与10 mg/kg相似的缓解率。然而,Besse博士表示,目前的标准剂量仍然“高得多”,并且“固定剂量是根据健康人的中位体重计算的,而不是通常体重较轻的癌症患者”。
真实世界中的低剂量证据
一项来自印度的真实世界研究表明,超低剂量纳武利尤单抗(每两周40 mg)联合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Besse博士认为,尽管这些生存数据不能直接与标准剂量试验相比,但生存曲线看起来非常相似。
Besse博士指出:“风险比似乎相似,就好像两种剂量下的生物学反应相似。这种方法在保持疗效的同时,将成本降低了86%。”
Ramalingam博士提到了另一项来自印度塔塔纪念医院的头颈癌研究,称其可以作为其他研究的范例,探索类似的方法,最终将这些药物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荷兰正在进行的DEDICATION-1试验正在正式比较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减量剂量(每6周300 mg或每3周100 mg)与标准剂量(每6周400 mg、每3周150 mg或每3周200 mg)帕博利珠单抗的疗效。初步结果显示,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率具有可比性。
当被问及这些发现时,Besse博士指出:“目前呈现的数据来自一项中期分析,该分析并未表明减量剂量有效。这项中期分析表明试验可以继续招募参与者。”
然而,Ramalingam博士提醒,在降低癌症治疗剂量时需要谨慎。
他在采访中说:“关于何种程度的剂量降低是合适的,目前知识不足。当然,当患者出现毒性时,可能需要进行剂量降低或暂停治疗。”
对于需要获取这些创新药物的患者,了解不同剂量方案的临床数据至关重要。MedFind提供海外靶向药和免疫治疗药物的代购服务,帮助患者获取所需药品。
延长治疗间隔
由Besse博士领导的PULSE试验正在研究在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维持治疗中,帕博利珠单抗是否可以从每3周给药一次改为每6周给药一次。
谈到延长免疫治疗间隔的经济影响时,Besse博士说:“如果这项试验结果积极,仅在法国,每3年就能节省10亿欧元。”他补充说,进行这项试验本身就能为医疗系统节省资金,因为试验组接受的帕博利珠单抗剂量减半。
优化治疗持续时间
关于治疗需要持续多久的问题,也存在减量的机会。来自法国国家医疗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停止帕博利珠单抗治疗2年后的患者,其总生存率与继续治疗的患者相似。
此外,III期DICIPLE试验表明,与继续治疗相比,在6个月时停止免疫治疗并未对无进展生存期或总生存期产生负面影响。停止免疫治疗还将3级或更高级别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降低了近10倍(2.9% vs 28.6%)。
监管挑战
Besse博士解释说,尽管减量治疗具有潜在益处,但面临着显著的监管障碍。即使临床试验证明较低剂量或较短疗程同样有效,药物说明书也可能不会改变,因为制药公司对此类改变缺乏动力。
他补充说:“我们需要修改临床指南,并通过学术激励机制游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及其他相关监管机构,以便修改说明书。”
Ramalingam博士也同意倡导基于证据的方法的重要性:“任何减量方法都应基于精心设计的随机试验的证据。学术界有责任进行此类试验,为临床实践提供信息。”
反方观点:何时“更多”更好
在ELCC 2025的一场辩论会上,Hye Ryun Kim医学博士提出了在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中使用靶向治疗时,支持延长治疗持续时间的论点。
Kim博士指出:“患者在治疗3年后仍面临复发风险”,并引用了ADAURA试验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奥希替尼停药后存在晚期复发。她主张在高风险患者中“尽可能长时间”进行治疗。
Rafal Dziadziuszko医学博士也在辩论中发表了不同观点,他区分了免疫疗法(描述为“细胞毒性”)和靶向疗法(描述为“细胞抑制性”)。
他认为,对于辅助或围手术期免疫治疗,1年或更短的疗程可能就足够了。相比之下,靶向治疗可能需要持续到疾病进展,以抑制残留的微转移灶。
然而,他指出,需要前瞻性数据来支持这一假设并确认最佳治疗持续时间。
未来的方向
当被问及哪种减量策略最有前景时,Ramalingam博士指出,最佳方法因具体情况而异。
他说:“关于免疫治疗的使用,有证据表明较低剂量和较短疗程可能同样有效。对于某些靶向治疗,剂量降低可能在保持疗效的同时改善耐受性。”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基于生物标志物的个体化治疗是制定减量策略的关键。
例如,Kim博士和Dziadziuszko博士强调了微小残留病灶监测的潜力,可用于识别真正需要延长治疗的患者。
Besse博士也看到了这种方法的希望。
他在采访中说:“通过循环生物标志物监测反应,可能使我们能够选择最佳反应者,并可能更早停止治疗,但这只是推测,需要得到证实。”他指出,PULSE试验将对此进行测试。
在设计减量试验时,Besse博士强调“患者至上,这些试验应以零风险降低疗效为目标,同时希望能降低毒性。”
他补充说,减量的理由必须非常充分,基于药代动力学数据和生物学原理。
面对复杂的治疗决策,患者可以通过MedFind的AI问诊服务,获取基于最新医学信息的个性化参考建议,辅助理解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