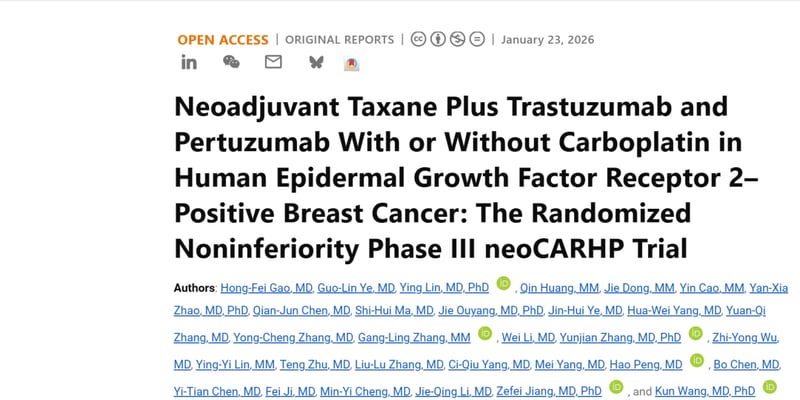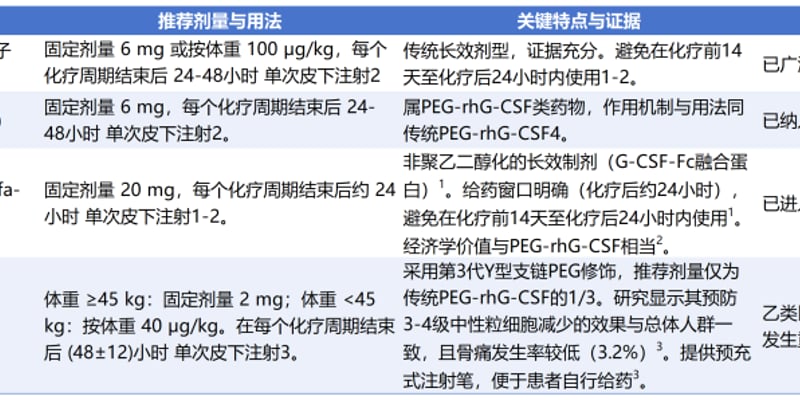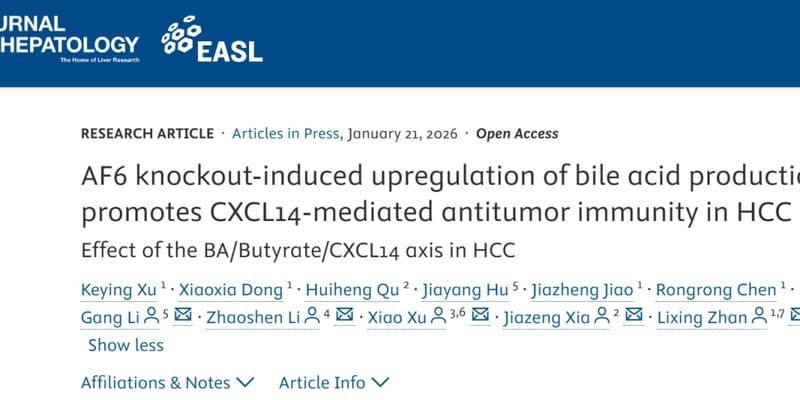子宫内膜癌肉瘤(ECS)是一种罕见且高度侵袭性的子宫内膜癌亚型,其预后通常不佳。这种双相化生癌由上皮和间充质成分组成,起源于肿瘤的上皮细胞,并通过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发展。约半数患者在晚期才被诊断,即使是早期患者,复发率也高达50%以上,导致五年死亡率居高不下。由于其罕见性,ECS的治疗方案一直缺乏前瞻性临床试验的指导,使得最佳治疗策略的确定充满挑战。然而,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精准医疗的飞速发展,针对ECS的病理学、分子图谱及新型治疗方法正不断涌现,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ECS的流行病学与风险因素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ECS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年增长率约为2%。非裔美国女性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白人女性。ECS通常被认为是老年疾病,发病高峰在70-79岁,但近年来诊断年龄有所下降,平均降至67岁。其他风险因素包括既往放射治疗、他莫昔芬使用、高体重指数、糖尿病、高血压、未生育、初潮早、绝经后发病以及外源性雌激素暴露。值得关注的是,林奇综合征和考登综合征等遗传性疾病也可能增加ECS的风险。此外,乳腺癌患者中ECS发病率的上升,提示可能存在尚未明确的遗传关联,例如与BRCA1/BRCA2突变携带者有关。
病理学特征与发病机制:上皮-间充质转化
ECS由恶性上皮(癌)成分和间充质(肉瘤)成分构成,两者界限通常清晰。传统上,ECS被认为是恶性混合性苗勒氏瘤,是子宫肉瘤中最具侵袭性的一种。关于其发病机制,目前普遍接受的是“转化学说”,即ECS起源于肿瘤的上皮成分,这些上皮细胞通过上皮-间充质转化(EMT)获得间充质特征。EMT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上皮细胞失去极性、细胞间接触,并获得迁移表型,这与癌症的局部侵袭和远处转移密切相关。E-钙粘蛋白的抑制和Snail1、Slug、ZEB1等转录因子的激活是EMT的关键驱动因素。尽管少数研究支持“碰撞学说”或“联合学说”,但基因组学、分子学和组织病理学证据大多支持ECS的单克隆上皮起源。
大体检查可见ECS常表现为体积较大、有坏死和出血的无蒂或息肉状肿块,可充满子宫内膜腔并突出于宫颈口。镜下观察,上皮成分最常见为3级子宫内膜样癌或浆液性癌,肉瘤成分则可分为同源性(如高级别间质肉瘤)或异源性(如横纹肌肉瘤、软骨肉瘤)。浆液性/透明细胞组织学类型和异源性肉瘤成分被视为不良预后因素。ECS的大体特征如图1所示。

图1
具有不同子宫内膜成分和分化程度的ECS如图2所示。

图2
肉瘤成分根据其是否与子宫组织相似,可分为同源性或异源性。最常见的同源性肉瘤成分是高级别间质肉瘤和未分化肉瘤,而最常见的异源性间充质成分是横纹肌肉瘤和软骨样分化。ECS的肉瘤成分如图3所示。

图3
分子图谱:揭示ECS的异质性
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将子宫内膜癌分为四个分子亚型:POLE/超突变型、微卫星不稳定/高突变型(MSI-H)/错配修复缺陷型(dMMR)、拷贝数高/TP53异常型(p53-abn)和拷贝数低/TP53野生型(NSMP)。ECS患者中,TP53异常型发生率最高(约73.9%),而POLE和MSI-H突变亚型则相对较少。这表明ECS的肿瘤突变谱主要由癌成分决定,且具有高度异质性。在具有子宫内膜样分化的ECS中,PTEN、KRAS、ARID1A和PIK3CA突变较常见;而在浆液性分化的ECS中,TP53、PIK3CA、FBXW7、CHD4和PPP2R1A突变占主导。值得注意的是,HER2/neu (ERBB2)扩增在约9%-18%的ECS肿瘤中被发现,这为靶向治疗提供了依据。此外,ECS病例中体细胞BRCA1/2突变的发生率也较高,分别为18%和27%。这些分子特征的深入理解,对于指导ECS的精准治疗至关重要。

表1

表2
诊断与预后:早期识别与风险评估
ECS的临床表现与其他子宫内膜癌相似,主要症状包括绝经后出血和盆腔疼痛。诊断主要通过子宫内膜活检或息肉状肿块活检,但术前取样准确性较低,最终诊断常需依赖子宫切除标本。影像学检查(超声、MRI、CT、PET)是诊断和分期的重要工具。围手术期血清Ca-125水平升高与不良预后相关。约一半患者在晚期被诊断,即使是早期患者,复发率也高达45%,导致5年死亡率达50%。不良预后因素包括肿瘤大小、肌层和宫颈受累、子宫破裂、分期不充分、异源性肉瘤成分的存在以及TP53突变等分子特征。
传统治疗方案:手术、化疗与放疗
由于ECS的侵袭性,无论疾病分期如何,多模式治疗都是标准方案。手术治疗通常包括全子宫切除术、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网膜切除术、腹膜活检、腹腔细胞学检查和淋巴结清扫。对于早期疾病,微创手术是可行的,但需避免肿瘤溢出。化疗在ECS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卡铂/紫杉醇联合方案常作为一线治疗。对于罕见的不可切除局部晚期病例,新辅助化疗后手术可能获益。放疗主要用于降低盆腔复发风险,但对远处转移的预防效果有限。联合放化疗,特别是“夹心”疗法,已被证明能延长总生存期。
新型治疗策略:精准靶向与免疫疗法
随着对ECS分子机制的深入理解,新型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正成为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通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和多塔利单抗(Dostarlimab),通过阻断PD-1与PD-L1的结合,重新激活T细胞对癌细胞的攻击。由于约58%的ECS患者中观察到PD-L1表达,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望成为治疗选择。在错配修复缺陷(dMMR)或微卫星不稳定(MSI-H)的晚期子宫内膜癌中,这些药物已显示出持久的抗肿瘤活性。然而,在微卫星稳定(MSS)或错配修复正常(pMMR)的ECS患者中,单药治疗效果可能不佳。图4展示了PD-1/PD-L1通路。

图4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仑伐替尼)联合使用,可能增强治疗效果。KEYNOTE-775 III期研究显示,对于错配修复正常的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二线仑伐替尼(Lenvatinib)联合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显著改善了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已批准该联合方案作为晚期或转移性子宫内膜癌的二线治疗。对于国内尚未上市或难以获取的创新靶向药和免疫疗法,患者可通过MedFind海外靶向药代购网站寻求帮助,获取所需的药品。
PARP抑制剂:BRCA突变患者的希望
鉴于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ECS病例存在体细胞BRCA1/2突变,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Olaparib)可能对这些患者有效。研究表明,具有同源重组缺陷和BRCA突变的ECS细胞系对奥拉帕利更为敏感。尽管相关临床研究较少,但已有病例报告显示PARP抑制剂在特定ECS患者中带来了临床获益。
HER2靶向药物:精准打击HER2过表达
约16%-19%的ECS病例存在HER2基因过表达或扩增,尤其是在浆液性或混合性癌成分中。HER2状态在原发肿瘤和转移灶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且不一致性是不良预后因素。NCCN指南推荐对晚期或复发性ECS患者进行HER2检测。对于HER2阳性的ECS,在卡铂和紫杉醇基础上加用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已显示出延长生存期的效果。此外,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等新型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也在研究中,有望为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TROP2靶向药物:新兴的ADC疗法
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在低分化子宫内膜腺癌和子宫浆液性癌中高表达,并与不良预后相关。靶向TROP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如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通过将细胞毒性药物精准递送至肿瘤细胞,有望成为ECS的新型治疗药物。
RAF/MEK抑制剂联合FAK抑制剂
对于存在RAS/MAPK通路基因突变的ECS患者,阿维替尼(avutometinib,一种RAF/MEK抑制剂)与地法替尼(defactinib,一种黏着斑激酶(FAK)抑制剂)联合使用,在病例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与单药治疗相比,可能带来更长的生存期。
上皮-间充质转化靶向治疗
由于ECS起源于上皮-间充质转化,通过阻断这一过程,使上皮成分保持主导地位,从而可以采用子宫内膜癌的标准治疗方法,并避免肉瘤成分占优等不良预后因素,这为未来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结语:展望ECS治疗的未来
子宫内膜癌肉瘤(ECS)作为一种预后极差的罕见癌症,其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尽管手术、化疗和放疗是传统基石,但新型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正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对ECS分子图谱的深入理解,特别是POLE、MSI-H、TP53、HER2和BRCA1/2等基因突变的识别,使得精准医疗成为可能。基于分子分类的辅助治疗有望显著提高患者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在探索这些前沿治疗方案时,了解药物的详细信息和获取途径至关重要。MedFind提供全面的抗癌资讯,包括药物信息和诊疗指南,助力患者做出明智选择。
未来,迫切需要开展更多基于ECS生物学特性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以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若您正面临子宫内膜癌肉瘤的治疗挑战,并希望了解更多海外购药或AI问诊服务,欢迎访问MedFind官网,获取专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