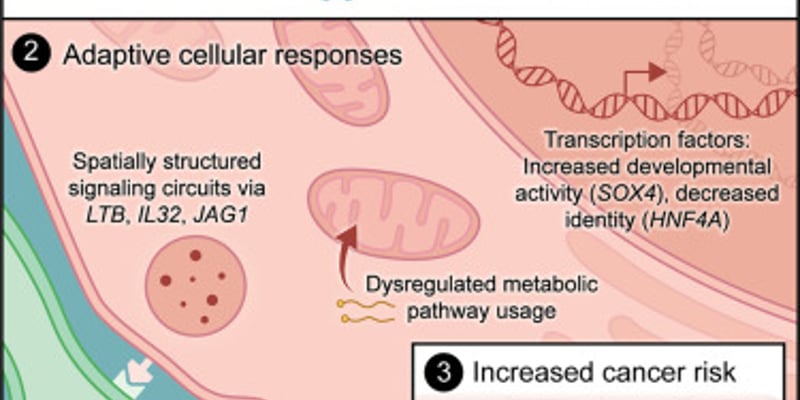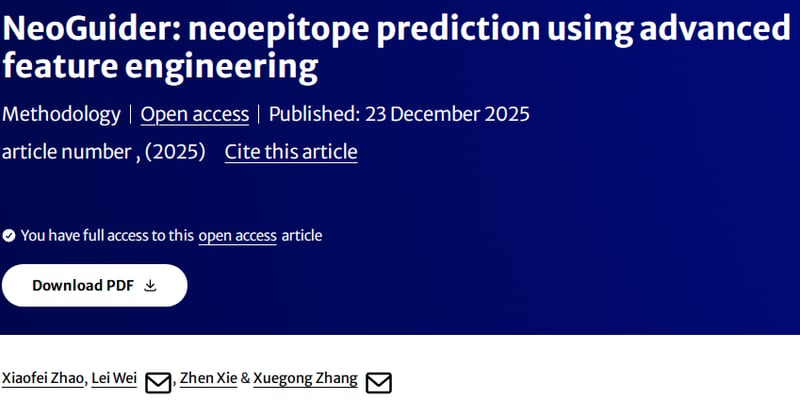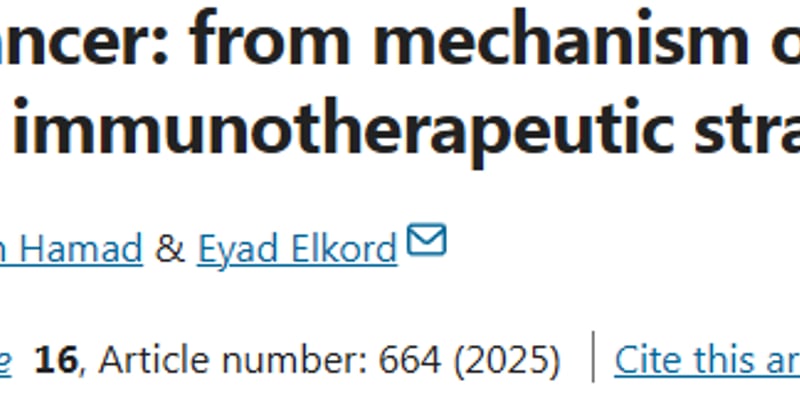传统的药物研发流程漫长且成本高昂,通常依赖于动物模型等临床前研究,然后逐步推进到人体试验。然而,近年来中国新药研发的飞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大量成功的临床试验数据,这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特别是美国的转化研究模式。现在,临床科学家们开始关注并尝试将这些来自中国的早期临床数据应用于美国人群。
中国在全球药物研发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2024年,中国贡献了全球高达23%的候选药物,仅次于美国。自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启动以来,中国肿瘤药物的研发数量持续攀升,并在2024年达到创纪录水平,预计2025年还将更高。中国药企的成功得益于其在人员配置和供应链方面的竞争优势,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推进研发。在中国,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从成立到获得首次人体试验数据可能只需18个月甚至更短,远快于美国。
然而,这种跨区域的数据应用并非没有挑战。美国FDA在历史上曾拒绝过仅在中国进行的癌症药物临床试验。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先前的研究表明,人种和民族差异可能会影响药物在人体内的最大耐受剂量(MTD)。例如,在日本进行的研究发现,细胞毒性药物和靶向抗癌药在日本人群和西方人群中的MTD存在差异,这被认为与内在和外在的种族因素有关。
那么,如何弥合这一差距呢?创新的“桥接研究”概念在证明仅在中国进行的早期临床试验数据对西方人群的适用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越来越多新药源自中国,桥接研究正成为美国药物开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肿瘤药物开发的最终目标是改善癌症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但生物技术公司面临着尽快将药物推向市场的巨大压力。桥接研究通过补充特定区域的数据来加速全球药物审批。
成功的桥接研究需要证明中国数据对美国的适用性,这要求研究必须纳入多样化的美国人群,包括黑人和西班牙裔患者;显示不同人种/民族群体之间药代动力学(PK)和药效学(PD)的相似性;并确认疗效和安全性与原始研究中观察到的结果一致。这些要素对于桥接研究最终获得FDA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至关重要。
作为一项由汉利康(Henlius)申办的针对小细胞肺癌(SCLC)的III期ASTRIDE临床试验(NCT05468489)的共同主要研究者,我亲身体验了桥接研究的复杂性。ASTRIDE试验旨在证明全球性但主要在中国进行的III期注册性ASTRUM研究的数据对美国人群的适用性。ASTRUM-004(NCT04033354)和ASTRUM-005(NCT04063163)研究已成功证实,PD-1抑制剂赛沃利单抗(serplulimab)联合化疗,在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和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与单纯化疗相比,显著改善了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尽管ASTRUM-005研究纳入了31%来自欧洲的白人患者,但由于缺乏美国参与者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群的代表性不足,FDA提出了担忧。作为回应,FDA建议汉利康收集额外数据,以证明ASTRUM研究结果对美国患者的相关性。经过仔细讨论和设计考量,ASTRIDE桥接研究应运而生。这项描述性研究计划招募每组100名患者,一组接受赛沃利单抗加化疗,另一组接受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商品名Tecentriq)加化疗。
ASTRIDE这类桥接研究的成功依赖于对先前已报告的临床试验数据的利用。FDA批准了ASTRIDE的描述性研究设计,而非优效性研究,原因在于全球性的ASTRUM试验已在一个大型非美国队列中验证了赛沃利单抗加化疗的疗效和安全性。ASTRIDE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展示相似的安全性、疗效和PK数据,来确认ASTRUM研究结果对美国患者群体的适用性,而非旨在证明统计学上的优效性或非劣效性。尽管描述性桥接研究的概念对于严格遵循传统临床试验范式的人来说可能显得非传统,但中国新药研发的快速步伐以及FDA致力于为美国民众提供全球最有效疗法的承诺,共同推动了这种灵活研究设计的出现。
了解这些前沿的临床研究进展,对于正在寻求最新靶向药或抗癌药治疗方案的患者至关重要。有时,这些药物可能首先在海外获批或有更便捷的获取途径。如果您对海外购药或仿制药的获取有疑问,可以考虑通过MedFind提供的海外靶向药代购服务或AI问诊服务来获取更多信息和帮助。MedFind网站也提供丰富的药物信息、诊疗指南等抗癌资讯,帮助患者了解更多治疗选择。
在后续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桥接研究中临床终点选择和试验设计的挑战,特别是在现有数据仅限于中国患者或对于预后较好的癌症而言OS并非可行终点的情况下。我们将探索在这些更复杂情景下,如何最有效地转化中国数据至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