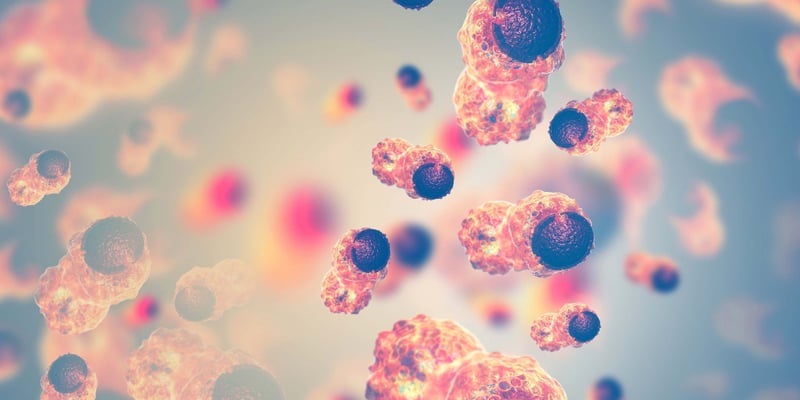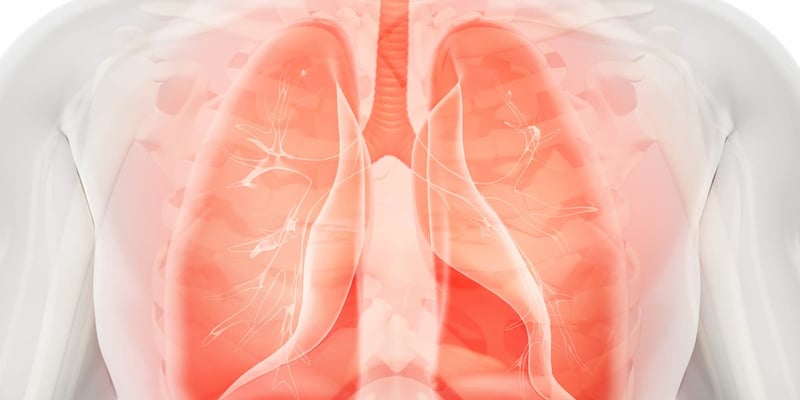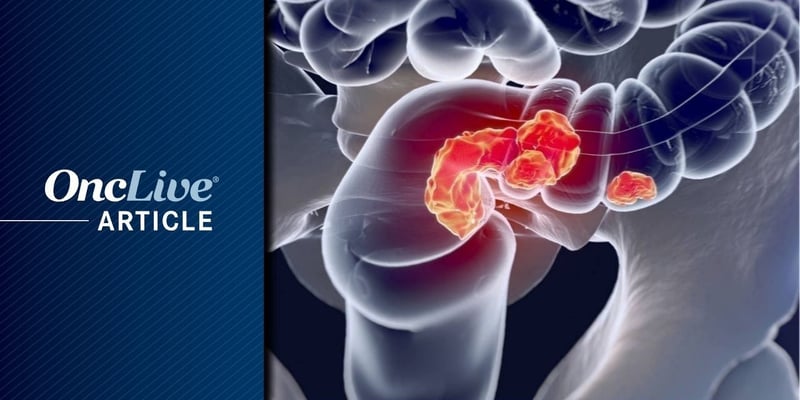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检测技术在血液肿瘤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它使得医生能够检测到治疗后体内残存的极少量癌细胞。然而,这项技术的普及也引发了对其生物学基础和临床指导意义的反思。《柳叶刀·血液学》(The Lancet Haematology)近期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就深入探讨了MRD作为生物标志物在血液恶性肿瘤(如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等)治疗中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MRD检测:从梦想照进现实
血液学的发展史上,从最初观察到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中癌细胞消失,到期望能检测“百万分之一的白血病细胞”以指导治疗,科学家们从未停止探索。如今,借助癌症免疫学、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定量PCR(qPCR)以及高通量测序等先进技术,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极高灵敏度的MRD检测,精确到百万分之一。
目前,MRD主要被用作预后生物标志物:MRD阳性通常预示着较高的复发风险,而MRD阴性则与较好的预后相关。然而,将其作为调整治疗策略(如是否需要加强治疗或停止治疗)的决策依据,其有效性仍有待更多验证。尽管美国FDA已支持将MRD作为多发性骨髓瘤等疾病新药审批的替代终点,加速了药物研发,但这并不意味着MRD在所有临床决策中都已成熟。
MRD作为生物标志物的生物学挑战
文章指出,将MRD检测结果直接等同于有活性的、能导致复发的癌细胞存在,可能过于简单化。
- 检测到的未必是“元凶”: 例如,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某些MRD阳性信号可能来源于非癌性的、终末分化的细胞,这些细胞本身不具备导致疾病复发的能力。
- 忽略细胞异质性: 残留的癌细胞并非完全相同,并非所有残留细胞都具有“种子”功能,能够引发复发。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中,早期检测到的PML::RARA转录本可能来自已分化、失去干细胞特性的细胞。
- 忽视微环境作用: MRD检测往往只关注癌细胞本身,忽略了肿瘤微环境和免疫系统等非肿瘤因素对疾病进展的影响。例如,在接受BTK抑制剂治疗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中,持续的MRD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差的结局,这提示微环境在抑制残留病灶中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这类复杂情况,患者和医生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必要时可参考[MedFind AI问诊](https://medfind.link/ai)获取辅助信息。
MRD指导治疗的临床证据困境
虽然多项研究证实MRD阴性与较低的复发率相关,但并非所有研究都观察到总生存期的显著改善。要让MRD真正用于指导临床决策,关键在于证明基于MRD状态调整治疗能够带来切实的生存获益。
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AML中,一些回顾性研究显示,对MRD阳性患者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改善生存,但缺乏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证实。目前,尚无充分的前瞻性数据表明,针对MRD阳性进行“抢先治疗”比等到疾病明确复发时再治疗,能在总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方面带来更优结果。
作者呼吁开展设计良好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比较基于MRD的适应性治疗策略与标准治疗策略的优劣,并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疾病类型设定比现有技术检测极限更高的MRD阈值。
谨慎解读MRD:未来方向与临床建议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尽管MRD在某些血液肿瘤(如ALL)中显示出价值,但不能将其成功经验简单推广到所有癌症类型。每种疾病背景下,MRD的生物学意义和临床证据都需要独立评估。
过度追求MRD转阴可能导致治疗强度过大,带来难以承受的毒副作用,反而损害患者利益。“清零”并非永远是最佳目标。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有治愈性手段(如移植、CAR-T)可用时,MRD可作为有价值的监测工具和治疗终点。此外,MRD也可能用于指导降低治疗强度,避免过度毒性,类似于PET-CT在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应用。
未来,需要更深入的基础研究,利用单细胞测序等新技术,结合类器官、人源化小鼠等模型,揭示癌细胞持续存在和复发的生物学机制。血液科医生在运用MRD指导治疗时,应审慎对待“反应越深越好”和“必须清除所有癌细胞”的假设,权衡利弊。获取全面的[抗癌药物信息](https://medfind.link/info)和了解不同[治疗方案的价格与获取途径](https://medfind.link/shop)对于制定个体化治疗计划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Lancet Haematol . 2025 Mar;12(3):e224-e229. doi: 10.1016/S2352-3026(25)0000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