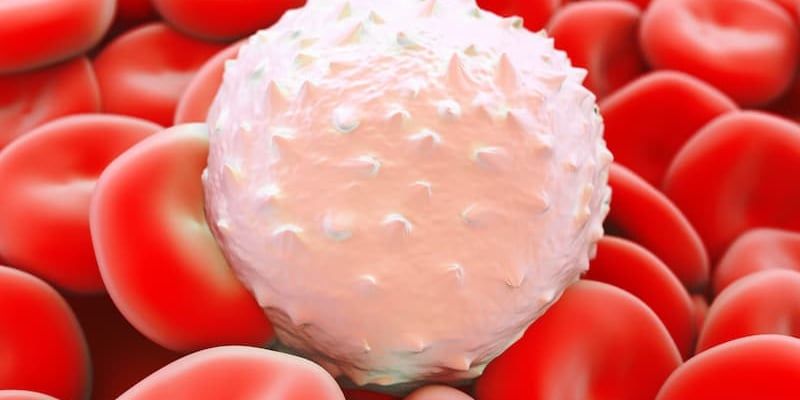肝细胞癌(HCC)作为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其复杂性与高致死率一直困扰着医学界。尤其在初诊患者中,多灶性HCC(即肝脏内出现多个肿瘤结节)并不少见,这些结节可能来源于肝内转移(IM)或多中心发生(MO),两者的临床预后和治疗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精准区分至关重要。
肝细胞癌(HCC)多灶性结节的微生物群异质性
近年来,肿瘤微环境中的微生物群在癌症发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调控肿瘤进展和促进转移方面。然而,对于多灶性HCC中不同肿瘤结节的微生物组成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这种异质性如何与宿主基因和转录特征相互作用,此前仍是未解之谜。一项由我国学者主导的开创性研究,通过对58例多灶性HCC患者的242个肿瘤结节和58个癌旁组织进行多组学系统分析,首次揭示了同一患者体内不同结节间微生物群的显著异质性,并深入探讨了其与肿瘤进化路径及转移潜能的紧密关联。
多组学方法揭示肿瘤微观世界
为全面解析这一复杂机制,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维度策略,对每个患者的多个肿瘤结节及配对癌旁组织进行了16S rRNA测序(分析微生物组成)、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检测基因突变)和转录组测序(RNA-seq,分析基因表达)。通过精密的系统发育分析和突变谱比对,研究将患者分为IM型、MO型及混合型。随后,结合微生物组成分析、功能实验和动物模型,验证了特定微生物在肿瘤进展中的作用。严格的微生物DNA提取、测序及数据去污染、标准化流程,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体外细胞共培养、小鼠原位移植模型以及无菌小鼠灌菌实验等功能验证,进一步阐明了特定细菌对HCC细胞迁移、侵袭和肿瘤生长的影响。
微生物群落差异与肝内转移(IM)关联
研究结果令人瞩目:多灶性HCC结节间的微生物组成呈现出显著异质性。令人惊讶的是,同一患者体内不同结节的微生物群落差异巨大,仅有3%的患者在不同结节中表现出相似的微生物组成。研究定义了高变异微生物(HVMs),发现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寡养单胞菌属(Stenotrophomonas)和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是最常见的HVMs。进一步的系统发育分析将患者明确分为IM-HCC、MO-HCC和混合型,其中IM型结节具有更高的主干突变率和遗传相似性,而MO型则突变共享率极低。微生物群落分析显示,IM结节和MO结节的细菌组成存在显著差异,IM结节的α多样性较低,且富含肠球菌属(Enterococcus)、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和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研究团队甚至利用9个细菌生物标志物构建了随机森林模型,能够以0.795的AUC值有效区分IM和MO结节,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新的生物标志物潜力。
EMT通路激活与免疫抑制微环境
转录组分析进一步揭示,IM结节中上皮-间质转化(EMT)通路显著富集,并且与IM结节中富集的细菌密切相关。例如,链球菌(Streptococcus anginosus)和肠球菌(Enterococcus spp.)与EMT相关基因(如CEACAMs、SLC2A1)呈正相关。功能实验证实,与粪肠球菌(E. faecalis)或咽峡炎链球菌(S. anginosus)共培养可显著增强HCC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在小鼠原位模型中,这两种细菌同样能促进肿瘤生长和肺转移,并诱导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表现为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增多和CD8+ T细胞功能下降。通过CODEX多重染色和空间分析,研究人员发现细菌富集区域与血管和MDSCs密切接近,提示细菌可能通过血源途径进入肿瘤。无菌小鼠灌菌实验进一步证实,粪肠球菌(E. faecalis)和咽峡炎链球菌(S. anginosus)可从肠道易位至肝脏,并促进HCC进展和EMT标志物表达改变。
图:多灶性HCC的微生物分布
对肝细胞癌(HCC)诊疗的深远影响
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多灶性HCC中不同结节的微生物组成具有高度异质性,并明确指出IM型结节中富集的特定细菌可通过激活EMT通路和塑造免疫抑制微环境来促进肝内转移。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多灶性HCC异质性的理解,更为未来利用微生物标志物进行精准分型和开发新型治疗策略(如靶向微生物群或EMT通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于正在寻求最新癌症治疗方案的患者而言,了解这些前沿研究进展至关重要。
MedFind致力于为癌症患者提供前沿的抗癌资讯,包括药物信息和诊疗指南,助您全面了解疾病进展。访问MedFind抗癌资讯,获取更多专业内容。如果您正在寻找海外靶向药,MedFind提供便捷可靠的代购服务,确保您能及时获取所需药品。了解更多,请访问MedFind海外购药。此外,MedFind的AI问诊服务也能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初步咨询,解答您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疑问。体验智能问诊,请访问MedFind AI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