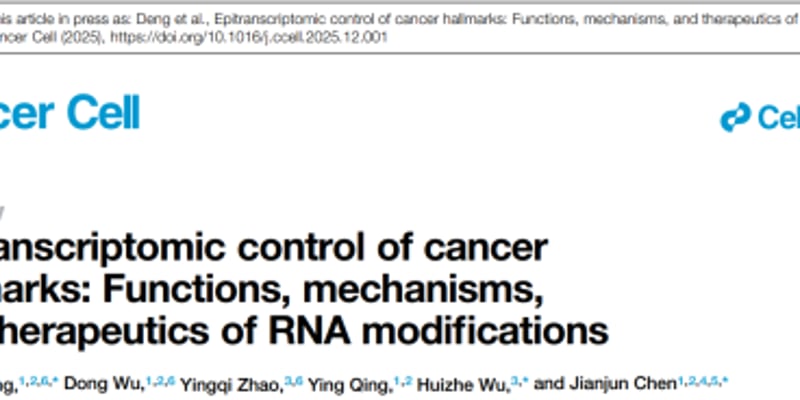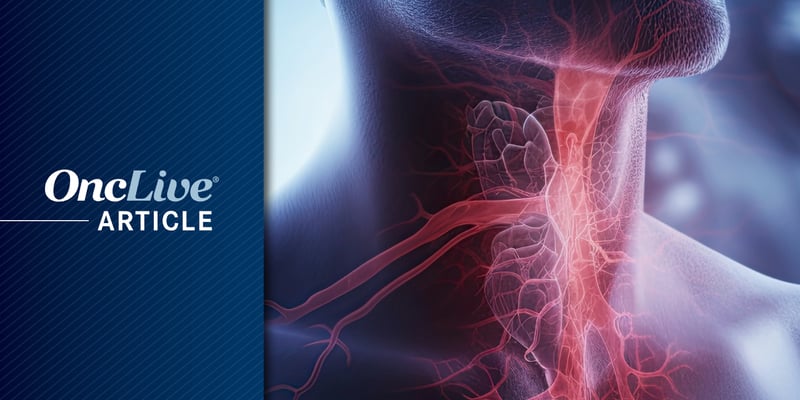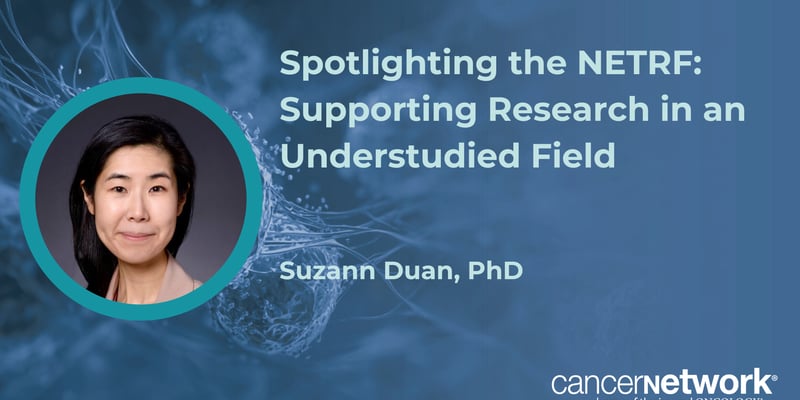引言
近年来,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的治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疗法层出不穷。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临床实践中的诸多“灰色地带”和不确定性。如何将这些创新疗法(如CAR-T)与传统方案(如移植)进行最佳整合,成为医生和患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将结合专家观点,深入剖析当前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的关键难题,特别是针对新诊断患者、功能性高危患者的治疗策略,以及CAR-T疗法的应用时机。
自体移植还是新药?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抉择
传统上,判断患者是否适合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主要依据其器官功能(如心肺功能)、体能状态等,年龄并非绝对的限制因素。然而,随着非移植方案效果的显著提升,这一标准正面临挑战。
例如,MAIA研究显示,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 商品名:Darzalex)、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的三药联合方案,为患者带来了长达五年的无进展生存期(PFS)。而更新的四药联合方案可能带来更优的疗效。这就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患者都接受移植?特别是对于70岁以上、移植时可能需要减少化疗剂量的老年患者,非移植方案或许能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这片“灰色地带”需要我们通过更多研究来明确。
四药联合方案: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新标准?
以达雷妥尤单抗联合硼替佐米(Velcade)、来那度胺(Revlimid)和地塞米松(Dara-RVd)为代表的四药方案,在临床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包括更高的缓解率、更深的缓解深度和微小残留病(MRD)阴性率,并显著延长了PFS。这使得“四药方案”逐渐成为所有患者的标准选择。
这种趋势改变了传统的治疗决策流程。医生可以在治疗初期就采用四药方案,根据患者的反应和耐受性来动态调整后续计划。例如,如果患者对四药方案反应良好且副作用可控,或许可以推迟甚至避免移植。反之,如果患者起初身体虚弱,但在治疗后状况改善(即“动态健康”),或对药物反应不佳,则可以考虑进行移植。四药方案的普及为实现个体化移植决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如何为“功能性高危”患者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功能性高危”指的是患者复发的时间比预期要早,但这与他们接受的初始治疗强度密切相关。随着治疗方案从双药、三药升级到四药联合移植和双药维持,对“功能性高危”的定义也在动态变化。通常认为,移植后1-2年内复发的患者属于此类。
对于这些预后不佳的患者,我们更需要积极采用创新疗法。因为他们疾病进展的风险更高,可能等不到后续的治疗机会。此时,CAR-T细胞疗法,如 西达基奥仑赛(ciltacabtagene autoleucel, cilta-cel; 商品名:Carvykti),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尽管CAR-T疗法存在神经毒性、继发性肿瘤等风险,但对于这些疾病已经“写在墙上”的高危患者而言,承担这些风险是值得的。
CAR-T疗法(如Carvykti)的应用时机与风险权衡
对于风险较低的患者,治疗选择则更为从容。例如,仅接受来那度胺维持治疗后复发的患者,使用基于CD38单抗(如达雷妥尤单抗)或蛋白酶体抑制剂(如卡非佐米)的方案,可能获得长达3年的PFS,且无需承担CAR-T疗法的潜在毒性风险。因此,许多患者可能不会立即选择CAR-T,而是将其作为后线治疗。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对多种药物耐药且早期复发的患者,尽早使用CAR-T疗法可能更有优势。数据显示,在治疗线数更少的患者中,CAR-T疗法的严重副作用发生率更低。例如,在CARTITUDE系列研究中,帕金森综合征的发生率从9%降至1%;继发性恶性肿瘤的风险也从高达10%降至约1%。这表明,在疾病负担较轻、患者身体状况较好时进行CAR-T治疗,不仅能有效控制疾病,还能降低严重毒性的风险。了解像西达基奥仑赛这类药物的详细信息、价格和购买渠道,对于制定最佳治疗计划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