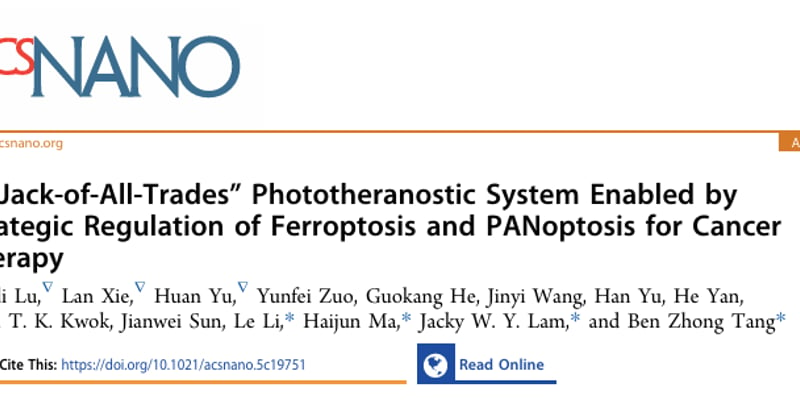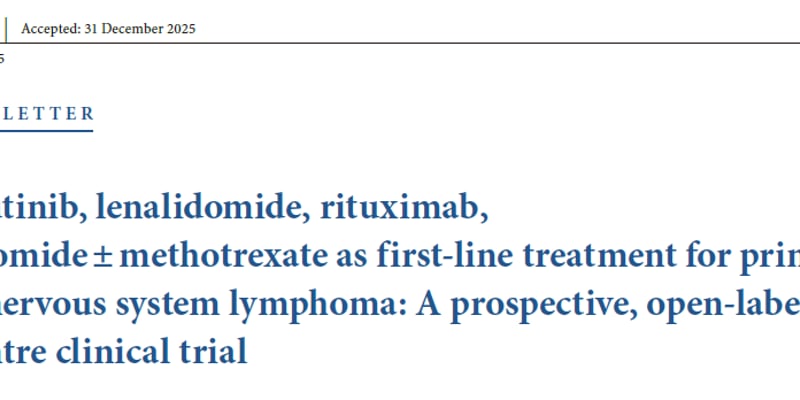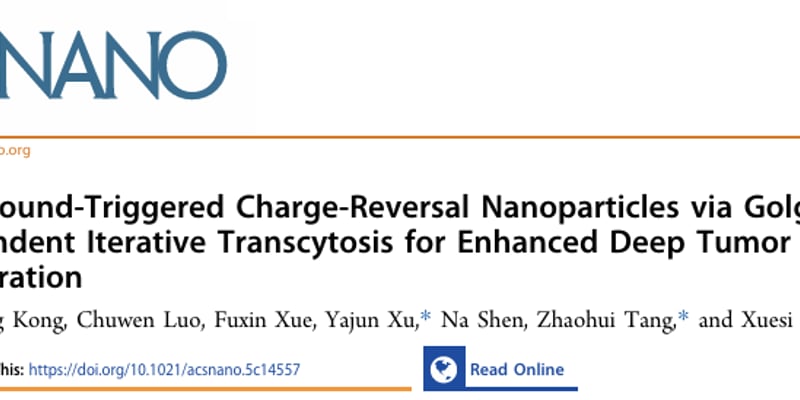引言:FGFR2靶向治疗的挑战
在肝内胆管癌(iCCA)的精准治疗领域,FGFR2基因融合是一个重要的治疗靶点,约有14%的患者携带此类突变。针对这一靶点,多种FGFR抑制剂(FGFRi)应运而生,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获得性耐药是靶向治疗普遍面临的难题,限制了药物的长期疗效。本文将通过一例真实的肝内胆管癌病例,深入探讨FGFR抑制剂治疗失败后可能出现的耐药机制,特别是PIK3CA和CDKN2A/B基因变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病例回顾:从有效到耐药的治疗历程
该病例的主角是一位43岁的复发性肝内胆管癌患者。基因检测显示,其肿瘤存在FGFR2-SH3GLB1融合,这是主要的致癌驱动因素。在接受了吉西他滨/顺铂和FOLFIRI方案化疗后,患者开始使用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仑伐替尼(Lenvatinib)进行治疗。
在仑伐替尼治疗初期,患者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实现了5个月的疾病稳定。然而,治疗10个月后,影像学检查显示肝、淋巴结及肺部转移灶出现进展。随后,患者尝试了FOLFOX方案化疗,但不久后又出现骨转移。此后,患者入组了一项临床试验,接受了另一款FGFR抑制剂英菲格拉替尼(Infigratinib)的治疗。尽管初期肝肺病灶稳定,但骨转移仍在进展。最终,患者在英菲格拉替尼治疗5个月后因病情恶化不幸离世。

▲图1 临床时间线及NGS结果
基因测序揭示耐药“真凶”
为了探究耐药原因,研究人员在患者治疗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多次下一代测序(NGS)分析。结果发现,在接受英菲格拉替尼治疗期间,从进展的骨转移灶活检样本中,除了持续存在的FGFR2-SH3GLB1融合外,还检测到了两个全新的基因变异:
- PIK3CA基因出现新的功能获得性突变(p.His1047Leu)
- CDKN2A/B基因发生纯合缺失
这两个新出现的变异被认为是导致FGFR抑制剂治疗失败、肿瘤产生获得性耐药的关键原因。PIK3CA突变能够激活FGFR信号通路的下游分子PI3K,绕过上游FGFR抑制剂的封锁;而CDKN2A/B的缺失则会解除对细胞周期的抑制,促进肿瘤细胞的失控性增殖。
耐药机制深度解析与未来方向
了解治疗耐药的机制对于制定后续治疗策略至关重要。传统的FGFR抑制剂耐药多与FGFR激酶结构域的继发性突变(如守门突变)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更换为不可逆的第三代FGFR抑制剂(如福巴替尼)或使用多靶点抑制剂可能有效。

▲图2 致癌FGFR2融合蛋白激活MAPK和PI3K/MTOR信号通路
然而,本病例揭示了一种不同的耐药模式:通过激活下游信号通路(PI3K/MTOR通路)和细胞周期通路来产生耐药。这种“旁路激活”机制使得肿瘤不再依赖于FGFR信号通路,从而对FGFR抑制剂产生抵抗。这一发现与在FGFR驱动的尿路上皮癌中的观察结果类似,在尿路上皮癌中,使用厄达替尼(Erdafitinib)等FGFR抑制剂治疗后,也观察到了PIK3CA突变介导的耐药。对于复杂的病情和治疗选择,患者可以尝试使用MedFind的AI问诊服务,获取个性化的信息参考。
这一病例强调了在靶向治疗进展后进行再次活检和基因测序的重要性。通过全面的分子特征分析,可以及时识别潜在的耐药机制,为患者寻找新的治疗机会。例如,针对PIK3CA突变,已有获批的PI3K抑制剂(如阿培利司);针对CDKN2A/B缺失,CDK4/6抑制剂可能成为潜在的治疗选择。未来,联合靶向FGFR和下游耐药通路(如PI3K或CDK4/6)的治疗策略,可能成为克服肝内胆管癌FGFR抑制剂耐药的新方向。获取更多关于肝内胆管癌的前沿抗癌资讯和诊疗指南,有助于患者和家属做出更明智的治疗决策。